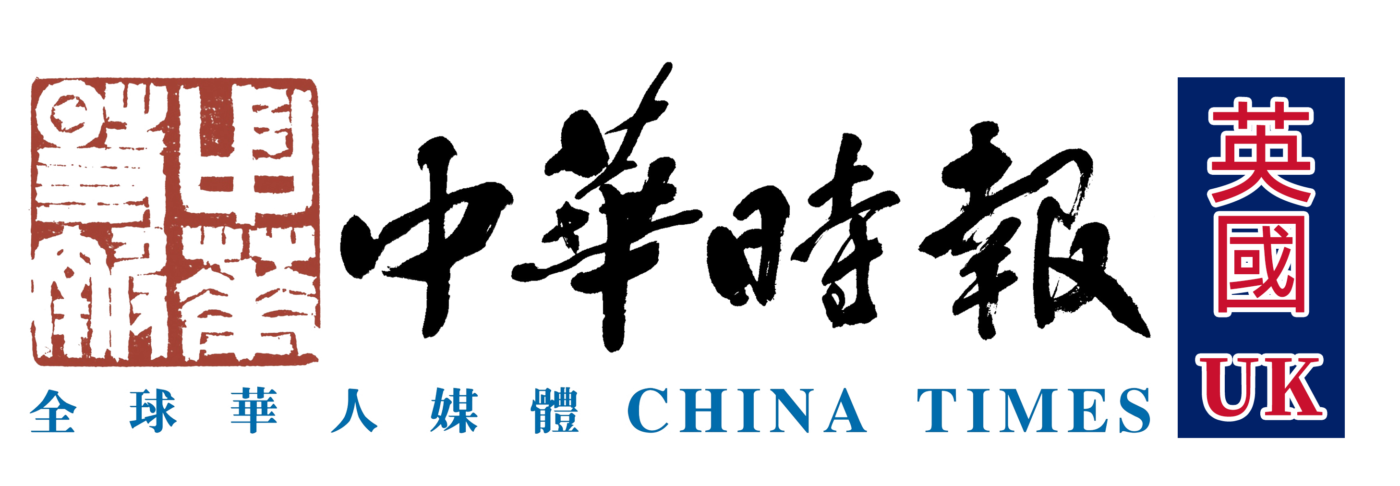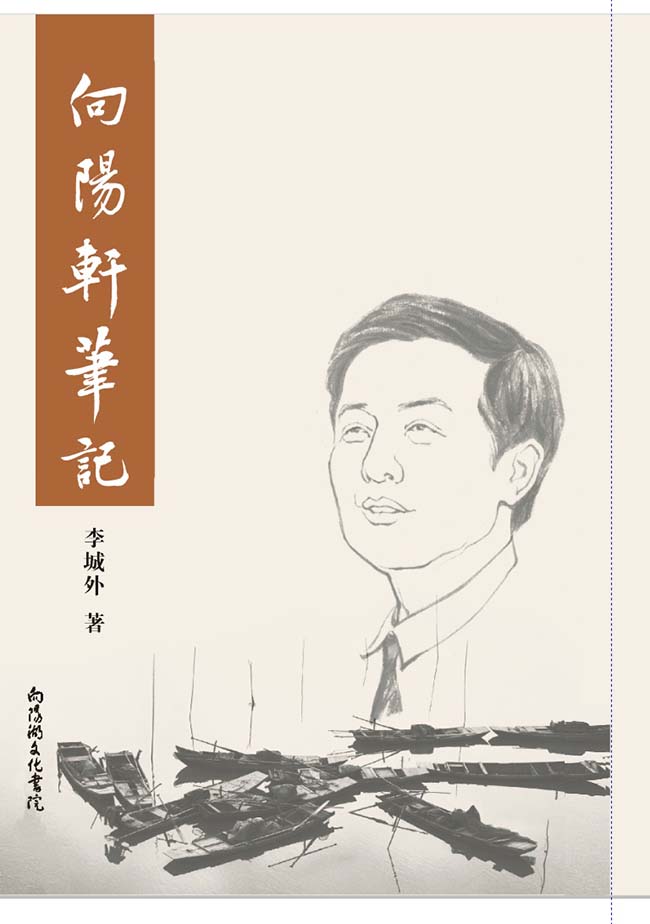
李城外
曾經有媒體記者朋友採訪我,問及最喜愛的作家是誰,最愛讀的作品有哪兩部?我的回答是錢鐘書的《圍城》,鄭逸梅的《藝林散葉》。
“愛錢”自不必細說,我收藏有錢先生《圍城》的各種版本,當年讀電大的畢業論文便是《試論<圍城>的諷刺與幽默》,甚至將原名李成軍改成了李城外。至於談起“戀梅”,我得多嘮叨幾句。對大名鼎鼎的“補白大王”鄭逸梅老先生,我是一見鍾情,通讀了他的全部著作,尤其是筆記,欣賞有加,常常從中享受到閱讀的快感。於是潛移默化,不知不覺當起民間“書記員”,利用零碎時間尋覓歷史遺存,打撈民間記憶。水到渠成,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在文學期刊《九頭鳥》開闢“鄂南文林散葉”專欄,歷時兩年,取筆名鄭小王,意為步鄭老後塵也。惜乎後來由於工作太忙,且主要精力花在向陽湖文化和五七幹校的研究上,筆記專欄臨時中斷,再未重新公之於眾。
好在近二十多年來,我一直在市直黨政機關和宣傳文化戰線擔任領導職務,還兼任過首屆市作協執行主席,尤其是長期擔任向陽湖文化研究會會長,有著得天獨厚之便利,受贈書籍頗多,且下大力氣收集地方文史資料和史志、年鑒、報刊,資訊量越來越大,手頭可順手拈來的素材越來越多,我一直在用心積累,一直在侍機重振旗鼓。加之交友多,閱歷廣,如今重拾散葉,於“文林”之外,又添“仕林”一族,桃紅李白,相得益彰,《向陽軒筆記》成書已初具端倪。
我個人始終認為,蒲松齡《聊齋志異》和洪邁《容齋隨筆》之存史價值與文學意義各有千秋,因為筆記這種野史的“含金量”或許並不亞於正史,由於記錄者均為有心人,不虛美,不隱惡,其真實性更值得珍惜。
可以說,本書算得上鹹寧地區建制以來第一部筆記文學作品。大人物與小不點同列,大題材和小浪花並存,我不敢說意欲將鹹寧文壇和仕林名人非名人一網打盡,將鄂南要事逸事故事一攬全收,若稱之為“民間鄂南文化史”和“坊間官場見聞錄”,卻是不容置疑的。隨著時間的推移,這批筆記還會與時俱進,續添數量,愈見份量。
值此《向陽軒筆記》初版付梓之際,感賦一首七律,以表心跡:“浪跡香城卅六年,笑吾忝列老溫泉。官場風雨恍如昨,文苑春秋渺似煙。掘礦淘金尋物語,吹糠見米綴花邊。向陽筆錄坊間史,始信聊齋可造田。”
2025年9月20日寫於向陽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