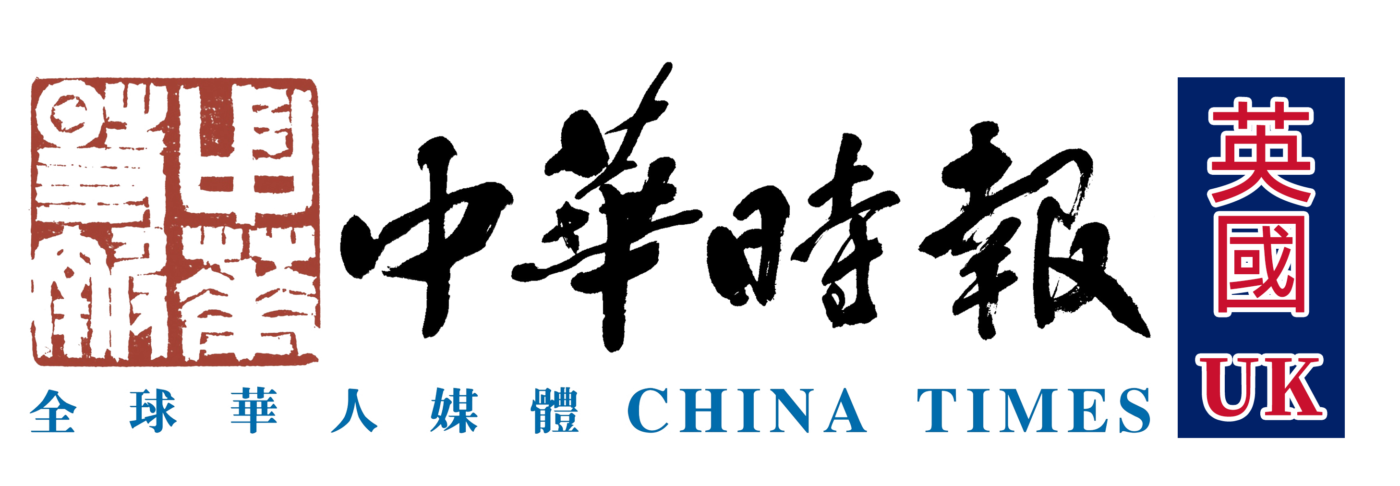佛门有云:“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少林方丈释永信从“佛门CEO”到阶下囚的戏剧性转折,不仅是一场个人命运的崩塌,更是中国宗教治理逻辑演变的缩影。十年前,同样的举报未能撼动其地位;十年后,他却因“旧账”被查。这其中的变与不变,恰如《金刚经》所言:“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唯一可得的,是时代对宗教边界的重新划定。
.jpg)
一、十年前为何“屹立不倒”?
十年前,释永信同样深陷“情妇、私生子、侵吞寺产”的舆论漩涡,却安然无恙。彼时,少林寺的商业化模式正符合“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的地方发展逻辑。释永信以“CEO方丈”的身份,将少林寺打造成年收入数亿的“宗教IP”,甚至成为地方政府的政绩名片。在“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语境下,只要不触碰政治红线,经济贡献足以抵消私德争议。 此外,当时的宗教治理尚未像今天这般强调“宗教中国化”的绝对性。释永信的海外活动,如率武僧团全球巡演、在欧美建分寺,被视为“文化输出”而非“宗教外交”。即便涉及商业纠纷或道德争议,只要不直接挑战体制,官方更倾向于“冷处理”。
二、十年后为何“墙倒众人推”?
十年后的今天,释永信却因同样的指控被查,甚至被注销戒牒。表面看,是“挪用资金”“违反戒律”等旧事重提,但真正的转折点,或许是今年2月他与教宗方济各的会面。
遭查,或因他在今年二月赴梵蒂岡,會見當時的教宗方濟各(左一)。圖為梵方發布當時雙方會面的照片。-圖/取自梵蒂岡新聞X平台.webp)
1. 宗教外交的“越界”风险 梵蒂冈是欧洲唯一与台湾“建交”的国家,中梵关系本就敏感。释永信以“文化交流”名义直抵教宗书房,在“宗教中国化”政策收紧的背景下,极易被视为“未经授权的宗教外交”。近年来,中国对宗教涉外活动的管控愈发严格,《宗教事务条例》明确规定境外宗教活动需报批。释永信的梵蒂冈之行,可能触碰了这条红线。
2. “宗教中国化”的刚性要求 过去十年,中国宗教政策从“引导适应”转向“绝对服从”。无论是天主教“自选自圣”主教,还是伊斯兰教“去阿拉伯化”,核心都是确保宗教不成为“境外势力渗透的通道”。释永信的海外网络(如全球分寺、国际交流)若脱离监管,可能被视为潜在风险。
3. 反腐与宗教整风的叠加效应 十八大以来的反腐浪潮无禁区,宗教领域亦不例外。中国佛教协会近年已有多名高僧被查,释永信案可视为宗教系统“清理门户”的延续。十年前,经济问题或可被“功过相抵”;如今,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基调下,任何污点都可能成为整肃理由。
三、宗教治理的“不变”逻辑:信仰必须服从政治
释永信案的深层启示,在于中国宗教治理的核心逻辑始终未变——**宗教必须服务于政治,而非挑战政治**。十年前,他的商业化被容忍,因其符合“发展”需求;十年后,他的国际化被清算,因其可能逾越“安全”边界。 《韩非子》有言:“不恃人之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宗教领袖的生存法则,从来不是“清规戒律”,而是“政治正确”。释永信的命运转折,恰如一面镜子,照见中国宗教的终极底线:你可以是文化符号,可以是经济引擎,甚至可以是国际名片,但绝不能是外交变量,更不能是政治隐患。
结语:
释永信的“十年之变”,并非个人善恶的因果报应,而是时代洪流中的一粒沙。佛经云:“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他的崛起,源于宗教商业化的时代机遇;他的陨落,则因宗教政治化的现实要求。此案过后,中国宗教界的生存法则将更加清晰——袈裟可以镀金,但不能越界;禅机可以玄妙,但不能僭越。
作者曾晓辉简介:
曾晓辉博士(1968-),广东龙川人。就读过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获南京大学天体物理学博士学位后转向艺术,师从雕塑泰斗潘鹤及油画家郭绍纲教授。
2000年创立广州新世纪艺术研究院。2009年在香港创办《中华时报》(现为全球华人主流媒体),并陆续拓展《中华新闻通讯社》、《中华摄影报》及英国《中华时报》。联合发起《中华电视》及世界华人流行音乐联合会。
现任香港美术学院及香港艺术研究院院长、多所大学教授,并任粤港澳大湾区艺术联合会主席、中华科技协会会长、世界监督学会会长等职。
学术著作丰富(艺术理论与历史)。雕塑创作富人文关怀,作品获全球多家美术馆、艺术馆典藏。积极参与国内外文旅规划(如张家界、贺兰山、上海及大坂世博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