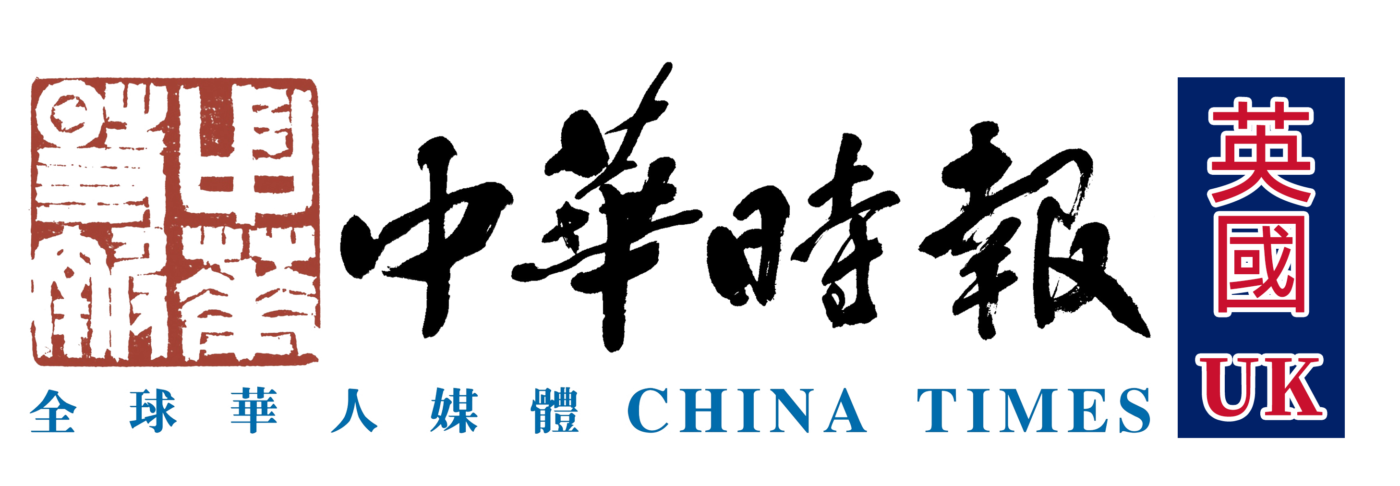晨光漫漶街衢時,昆明理工大學齊教授的車已在洲際酒店階前泊成一句無聲的邀約。她引我們至1903商圈,網紅米線店前人潮如沸,取號單上十餘位等待者名字疊成小山。“饑腸轆轆等叫號,不及師者一諾重。”她為款待我們,竟將廣東門生與故交的晚約輕輕推後,這份情誼在春城的薄霧裏淬出暖光。

轉進“滇滿樓”,滿牆的榮譽證書在燈下泛著檀木光澤。九十八元的過橋米線端上時,小橋般的配料橫渡青花大碗公,熟食如彩貝綴於浪尖。湯氣蒸騰間,多年前東盟論壇後那場米線夜宵驀然浮現——十指不沾陽春水,為君熬盡骨湯濃。這白玉細絲何止是舌尖之橋?分明是情義的舟楫,在歲月長河擺渡著相逢的重量。

第一省:吾心待客誠乎?

湯霧嫋嫋如禪香,齊教授為新朋擱舊約,盛意已化入骨湯。諺雲:“米線不過橋,枉作雲南行”,人間至味原是真心真意慢火熬。

午後循宗親廣春要求,踏入雲南師大的西南聯大舊址。昔年弦歌沸地處,唯餘一爿鐵皮小屋匍匐在烈士紀念碑的巨影下。那“剛毅堅卓”的校訓,原是烽火中淬煉的脊樑——自盧溝橋月碎,三千師生分兩路南渡:一路繞道安南輾轉,一路組成“湘黔滇旅行團”,以草鞋丈量一千六百里破碎山河,書箱作盾,筆桿為矛,在硝煙裏辟出這方杏壇。八載星霜雖短,卻孕出漫天星斗:兩彈呼嘯刺破長空,諾獎光芒照亮人類暗夜。

第二省:吾志承先賢乎?

鐵皮屋如一枚生銹的圖釘,將歷史牢牢鉚在滇土。書生負笈越千嶂,小屋雖仄,撐起的卻是華夏脊樑。所謂銅皮屋裏千秋在,正是這般剛毅在時光中錚錚迴響。

赴羅府約時遇打車風波。司機見我唇含雪糕,一句“弄髒車廂”如冰錐刺入暖陽。幸而轉車脫困,終抵友人雅舍。見他自紫陶罐珍重取出一餅老普洱,茶刀輕啟時,陳香似蟄伏的歲月驟然蘇醒。“這茶與我同庚。”他笑言。紅棉紙包裹的茶餅遞來時,分明是十餘載情誼的結晶。琥珀茶湯入喉,溫厚茶氣頃刻融解心頭霜淩。晚宴設於“老銅鍋魚”店,牆繪古滇國魚紋盤桓,銅鍋沸浪翻滾江川舊夢,魚躍湯沸間,千年漁火在蒸氣裏明明滅滅。


第三省:吾行克己恕乎?
冷語似雪沁肌骨,幸有陳茶知己慰風塵。茶逢舊雨湯愈釅,銅鍋沸處古意醇。世間炎涼事,終歸心鏡映——胸襟若陳年普洱般溫厚,方見春城無處不飛花。
七律·滇橋夜泊
金匙玉碗渡香塵,十指熬春是此身
鐵皮屋小擎星漢,銅鼓雷驚醒月輪
廿載陳茶知己獻,一江活水故人魂
天公也作留客雨,踏碎銀珠步步春
—
夜色漸濃時,行囊裏齊教授薦的鮮花餅與羅友贈的普洱相依而臥。收拾行篋之際,窗外驟起驚雷,十萬銅鼓震徹雲霄,銀箭般的雨矢急射窗櫺。行囊半啟處,茶餅竟與雷聲共振低鳴——莫不是滇山張臂挽行客?花香茶韻交織升騰,將翠湖煙柳、鐵屋風骨、銅鍋漁火盡收囊中。
雷聲滾過屋簷如天公浩歎,雨簾垂落似春神垂珠。那碗渡情之米線,那間鑄魂之鐵屋,那餅凝誼之陳普,那鍋沸浪之鮮魚,早化作靈魂行篋裏的壓艙石。茶餅裹紅紙,米線渡心橋,這滇雲水土,已在血脈裏長成另一座無雨的春城。
明朝辭滇馬蹄疾,且看電光裂長空。忽悟臨行雷雨非別淚——
原是銀河傾盞,以九天醴泉為我餞行。踏雨成蓮處,步步生春痕。
劄記尾注:
米線金橋渡肉身,聯大鐵屋渡精魂,陳年普洱渡歲月,終在雷雨夜悟得——雲南贈我三重渡,我報滇雲一葦航。歸途煙雨漫香江,行囊中茶餅忽有微溫,原是春城在血脈深處續上了暖爐。
2025.7.19夜於昆明洲際酒店
作者:曾曉輝,天體物理學博士、雕塑家,中華報業集團及中華時報傳媒集團創辦人。他於2000年創辦廣州新世紀藝術研究院,2009年在香港創辦《中華時報》,2012年創辦《中華新聞通訊社》和《中華攝影報》,並於2017年在倫敦創辦英國《中華時報》。他還是《中華電視》及世界華人流行音樂聯合會的創始人之一。
目前,曾博士擔任香港美術學院及香港藝術研究院的教授與院長,同時擔任粵港澳大灣區藝術聯合會主席、中華科技協會和世界監督學會會長,以及多所大學的兼職教授。他曾在中國大陸的相關機構(包括廣州市政府、廣州馬會、廣東省鐵路監理、廣東省演出協會、廣東省南越國文化研究院)等擔任高級職務。其藝術作品廣泛分佈於全球,已被多家美術館和博物館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