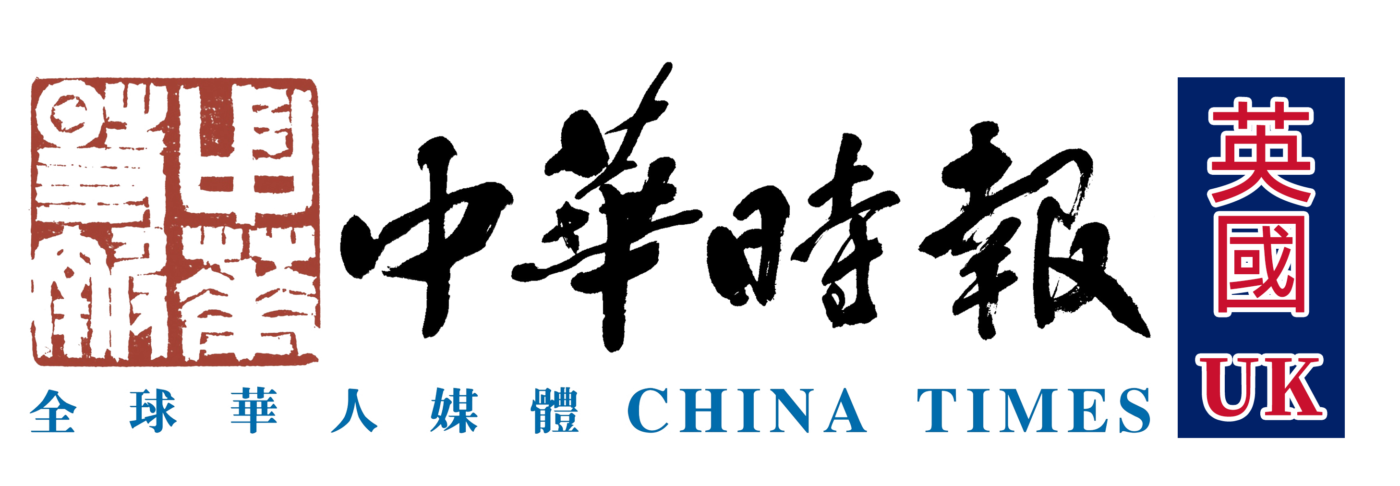作者:吳典憶
2001年,美國《華爾街日報亞洲版》選出了過去一千年中全世界最富有的五十人。其中,上榜的中國人有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珅、劉瑾、伍秉鑒和宋子文六人。相較於其餘五人,伍秉鑒的名字稍顯陌生。但是,這位傳奇般的廣州十三行總商本不應在歷史長河之中沉寂。
伍秉鑒,字成之,號平湖。生於乾隆三十四年(1769),終於道光二十三年(1843)。他所出身的怡和行伍氏家族是十三行中最具影響力的潘、盧、伍、葉四大家族之一。

據史料記載,“平湖(伍秉鑒)年未弱冠,即命開枝貿易。”伍秉鑒小小年紀便已跟隨長輩經商,這既為他積累了商業經驗,開拓了視野,也使他在突逢變故時能夠處變不驚。嘉慶六年(1801)其兄伍秉鈞不幸早早去世,主持怡和行業務的重任就此落到了伍秉鑒的身上。他所具有的沉著、冷靜的性格在此時體現出來,不僅有條不紊地安排料理了兄長的後事,還在給外商的書信中寫到:“至小行生理各事,俱照家兄生前,如常辦理。”
短短兩年後的嘉慶八年(1803),伍秉鑒便被眾行商推選為總商,與盧觀恒共同主持十三行的事務。怡和行伍家成為了十三行行商的領頭者之一。嘉慶十二年(1807),怡和行的身家已上升至第二位,僅次於同文行。
伍秉鑒憑藉出眾的商業能力為他自己積累了大量財富,但他並非唯利是圖、為富不仁之輩。在追求利益的同時,他奉“義以生利,義利統一”的經商理念為圭臬,以“誠”為致富之路。嘉慶十三年(1808),一家英國公司投訴怡和行售出的一批生絲品質不合格,伍秉鑒親自到貨倉驗貨,確認確是次品後,當即對英國商人保證將次品收回,三日內換為合格生絲。這樣光明磊落、不為錯誤諱飾的態度為怡和行贏得了英商的信任。次年,怡和行便首次登頂十三行之首,時人稱浩官(外商對伍秉鑒的稱呼)已然成為“廣州商界一個重要人物”。嘉慶十八年(1813)原總商去世後,伍秉鑒正式成為十三行行商的新總商,史稱其“多財善賈,總中外貿遷事,手握貨利樞機者數十年。”
怡和行屹立數十年不倒,與伍秉鑒明察謹慎、義利並重的為商之道關係密切。道光三年(1823),一名買辦挪用怡和行作保的一家美商行號庫款未歸一事被伍秉鑒發現,伍氏當即將短少的五萬元款項送還該行。同年,一位破產的波士頓商人因欠怡和行七萬餘兩銀元而無法回國。伍秉鑒對他說:“你是我的第一號‘老友’。你是一個誠實人,只不過是不走運。現在我將欠款期票當面斯毀,把欠款一筆勾銷。你可以回國了。”這名商人十分感動,回國後大力幫助伍秉鑒在美投資。至19世紀初葉,怡和行儼然已經成為一家名副其實的工商業跨國大財團,投資著美國的房地產、石油、鋼鐵、電報等各類行業,還由福布斯代為投資經營著證券業。伍秉鑒在美國的投資是如此巨大,史載其“有買賣生理在美利堅國,每年收息銀二十餘萬兩(銀元)”,以至於美國有一艘商船以他的名字命名為“伍浩官號”。
伍秉鑒是怡和行最核心的人物,正是在他掌管的時期,怡和行和伍氏家族走上了繁花似錦、烈火烹油的巔峰。印有怡和行圖示的貨物即被認可為上品,這便是怡和行當時卓越的品牌公信力。有洋商評價伍秉鑒是“一個最有用的行商。…擁有大量資本及高度的才智,因而在全體行商中,居於卓越的地位。”時人稱“嘉慶間安海伍氏物力最富,……每遇歲除,家庫核存常達千萬有奇”,伍家可謂富甲一方。據W.C.亨特的《廣州“番鬼”錄》記載:“浩官究竟有多少財產,是大家常常談話的話題,但有一次,因為提到稻田、房屋、店鋪、錢莊,以及在美國、英國船上的貨物等各種各樣的投資,在1834年(道光十四年),他計算一下,共約值2600萬兩(墨西哥鷹洋銀元)”。而當其時,美國最富的皮毛大亨約翰·雅各布·阿都斯的財產僅有2000萬美元,清政府一年的財政收入也不過4600萬兩銀元,伍秉鑒世界首富之名當之無愧。
伍秉鑒能夠取得如此成績,並不因其工於心計。注重合作,誠信經營,高度的使命感和責任感,“義以生利,義利統一”的價值觀……因為具有了種種他人無有的品格,所以才鑄就了一個如彗星般璀璨的商業帝國。但是,正當伍秉鑒放眼世界、大做歐美生意時,1840年(道光二十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了。在英軍直沖珠江口的堅船利炮之下,伍秉鑒的商業藍圖乃至整個商業帝國褪色了。三年之後的道光二十三年(1843),伍秉鑒在失落、不甘、悲戚、憂患的環繞下離世,享年74歲。伍秉鑒的離去似乎也預示著十三行熱烈如繁華烈火般的時代的終結。道光二十二年(1842),中英簽訂《南京條約》,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口通商,十三行壟斷對外商貿的歷史就此徹底結束。
實際上早在19世紀初,十三行的行商們就已在紛紛設法脫身。因為不從此中脫身便往往是破產、抄家、流放的結局,最終只能是身不由己地紛紛走向崩潰。成功如伍秉鑒,也在與官府和洋商的交涉中身心疲憊,於道光六年(1826)離開商界,將苦心經營的怡和行傳給了下一輩。
官府敲詐,外商欺淩,種種複雜因素造成了十三行的黯淡收場。實際上,十三行與其說是一個經濟單位,不如說是清政府“以官制商,以商制夷”思想的產物。它自設立伊始便始終處在朝廷的高度掌控之下,背負著朝廷和外商有形無形之中的種種擠壓。行商們的資本大多並未形成積累,以各式各樣的緣由成了效勞官府的禮物。重農抑商的國家政策也成為他們發展的枷鎖。各種因素綜合作用導致了此時中國的外貿完全是有來無往的被動狀態,嚴重阻礙了中國商人和商業的發展。說到底,沒有國家政策的支持和鼓勵,起步階段的產業與易折的花朵無異,在外敵環伺的險境中只可能艱難求生。內外交困的十三行最終在鴉片戰爭的硝煙中轟然倒塌,乃是歷史發展的必然。